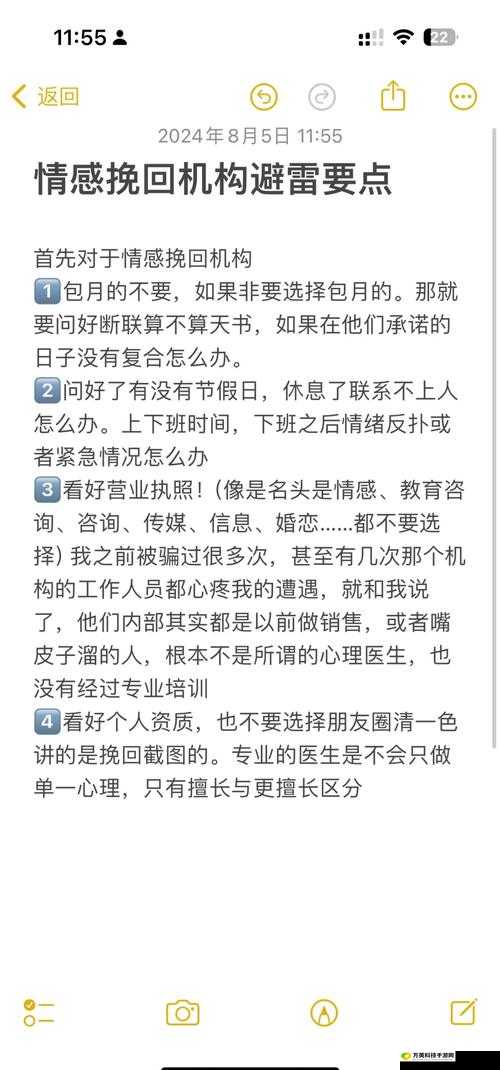当欲望披上成人外衣——色情行业中的「裸体刷」究竟是人性还是陷阱?
荧幕蓝光里滚动的弹幕总让我想起医院急诊室的白色灯光。那些飘过屏幕的「求资源」「看无码」不是简单的文字,是无数人蜷缩在椅背上的战栗。城市立交桥下的ATM机吞吐着纸币时,隔着玻璃能看见五百米高空旋转餐厅里,西装革履的策划正在讨论新一季「刷」算法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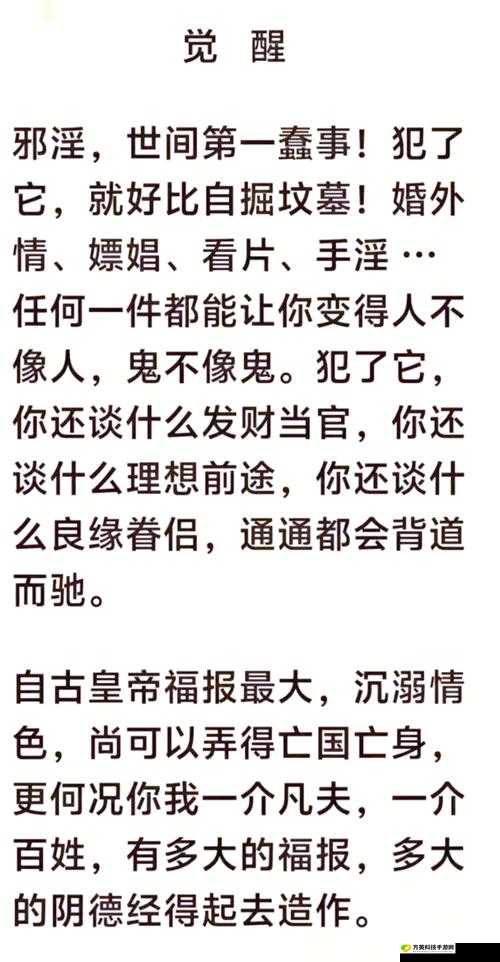
从洞穴壁画到算法推荐
五万年前拉斯科洞窟的野牛侧影,和如今服务器机房闪烁的LED灯之间,隔着太多权力的游戏。当原始人用赭石涂抹岩壁时,他们渴望征服的不是动物,而是对未知的恐惧。而当程序员调试「美女」推送模型时,他们用1和0编码的不是欲望,是资本对人类脆弱性的精准打击。
深夜十二点的旺角街头,便利店海报上的明星侧脸和视频截图的边缘光影竟有惊人的相似。霓虹灯管下的理发店里,年轻男孩对着手机笑出声音,却不知自己正参与一场跨国资本的狂欢派对。
裸体的七个谎言
有人在知乎提问:「为什么现代人越富裕越依赖黄片?」这问题像问「为什么雨水会打湿翅膀」。柏林墙倒塌的那年,俄罗斯某小镇超市老板开始在香肠货架下压着裸体明信片,后来成为当地首富。
现在随便点开某个算法平台,系统会用三秒判断你更偏爱「3P」「酒店」「萝莉」还是「丝袜」。这些冰冷的分类标签下,漂浮着无数人的孤独像未读消息永远闪动。2022年联合国人口报告指出,85%的用户在下载所谓「资源」时,同时打开了至少4个社交软件。
陷阱就是我们的主场
去年香港廉政公署查封的「裸体刷」案件里,涉案服务器藏在葵涌工业邨普通铁皮屋。屋檐下的巨型空调在午夜轰鸣时,像极了日本AV女优美树做成熟表情时发出的低笑。
那些标榜「真实体验」的虚拟舱室里,年轻人戴着VR设备呕吐时,脑后银头皮线正默默记录着瞳孔扩张的毫米数据。摩洛哥集市卖丁香的老人说,现在的游客更爱买预先粉碎的药粉,就像我们宁可吃外卖也不肯自己煎煮的草药。
女性凝视的暴力美学
当镜头持续37秒聚焦某个部位时,摄像机里藏着枪膛。佛罗伦萨学院美术馆的米开朗基罗原作前挤满游客,而某个服务器机房一整排硬盘里,却存着比西斯廷教堂多十倍的凝视。
巴黎女记者西蒙娜·德·波伏娃在六十岁时写下:「欲望是最需要被言说的秘密。」可当资本把它装进塑料袋,放进自动贩卖机,欲望就变成了可以扫码支付的罐头。东京涩谷站前的机械姬广告牌每天傍晚亮起时,街角的流浪猫总要对着霓虹闪烁处蹲守三个小时。
我们都是数据海洋里的金枪鱼
深夜三点四十五分,我的邻居工程师在书房修改人脸识别模型参数。隔壁房间,他14岁的女儿正在对比不同平台「成片」的压缩画质。当马斯克的星链信号穿越大气层时,某个美国对冲基金正在通过斐波那契算法预测日本成流出货量。
智利诗人聂鲁达曾用四十首诗写爱,而现在需要用2.1MB的RAR密码解压。布宜诺斯艾利斯码头装卸的集装箱里,除了牛肉罐头就是刻着「XXX」的黑胶唱片。
黎明前的麦克白夫人
柏林墙倒塌第三十年,那位卖裸体明信片的俄罗斯老板开了网红咖啡馆。吧台后挂着年轻时的照片,上面戴着苏联军官徽章,正对收银台二维码。
纽约时报曾算过账:观看一小时所谓「成片」消耗的脑电波能量,相当于连续阅读九歌整部。而我们正用观影时分泌的多巴胺,为某个岛国股市持续供能。
灰度滤镜下的生命狂欢
釜山电影节某次开幕式上,导演李沧东被问及作品里的女性角色设置。他说:「真正的性感是削苹果时溅起的汁水在裙摆上的瞬间。」此刻釜山港凌晨两点的鱿鱼市场,货车车厢上贴着黄蔷薇招贴,这朵花在中东某社交平台上被称为「世界最贵的表情符号」。
在虚实交错处寻找诗与远方
西班牙画家弗朗西斯科·戈雅晚年画裸体的马哈,玛丽亚·路易莎公主看了三次都没认出画中人是自己。如今我们在算法构建的牢房里,同样认不出数据海洋里那些被切割的碎片,都是曾鲜活跳动的心跳。
数据流中的蝴蝶振翼
曼哈顿中城某投资银行的交易员在交易簿上画着三点式泳衣速写时,莫斯科交易所正因某平台更新暴跌7%。当我们的凝视穿过光纤穿越重洋时,可能在光纤接续盒产生折射,折射里有非洲某村庄建新学校的希望。
写给下一代的密语
清迈大学人类学系有个研究项目:对比不同年代人类的凝视轨迹。他们发现智能手机时代,我们眼球每秒跳动频率比原始人快47次,却很少停留超过3.2秒。这让人想起梵高的星空,笔触翻卷着对永恒的渴望,而我们正在用零点几秒的凝视,兑换某种虚假的瞬间。
此刻印度恒河边的法显译经处,暮鼓声正盖过直播平台「刷」单声。当古老的贝叶经文与翡二十六字体相遇时,我突然明白:人性永远在算法与灵魂间摇晃,就像永远在找找寻不到的Wi-Fi信号。
关掉所有屏幕后,我常听见窗外的猫在念叨数字密码。它们对着月光摆出的种种姿势,远比荧幕里的表演更令人心碎。或许某天,我们终将学会用真实存在来交换短暂眩晕,就像老城茶馆里,摆着玛瑙核桃的老者总要比拿着按摩仪的年轻人活得长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