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囚禁的蔷薇_东宫禁脔背后的欲望与尊严
初见夏如意入东宫那日,花蒂正盛。青石阶上铺着三层猩红锦缎,她跪在第二层边缘,指尖戳进绸缎细密的褶皱里。这丫头穿着月白色宫装,袖口的暗纹绣着北方不常见的锦鲤,脂粉未施,眉眼却像被雨水泡过的墨迹,晕染开来格外深邃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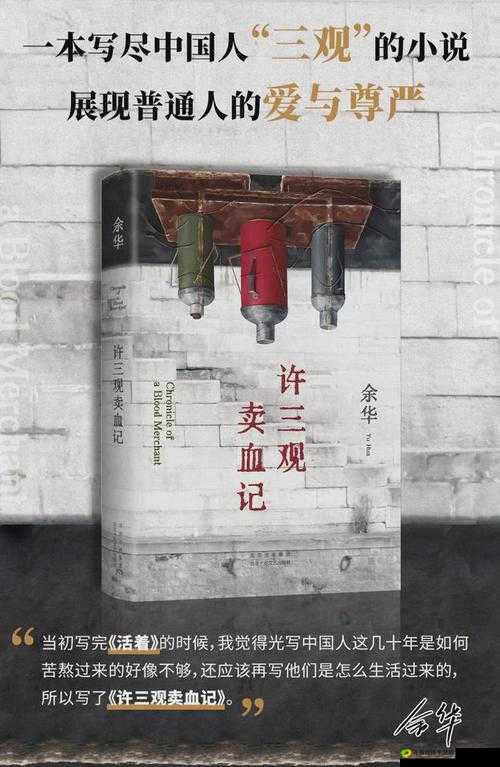
敬事房的嬷嬷私下嘀咕,说这新人手脚细长,倒生得一副读书人的骨架。话音未落,就听见东宫偏殿传来瓷器摔碎的闷响——那可是太液池畔养着三年的春梅枝头,枝干虬曲盘旋,嫁接过十二种花蒂。
我总在想,若要论世间最教人七窍生烟的物事,大概就是明晃晃的金雕殿宇下,那些藏在绸缎里的东宫禁脔。君王执掌江山如执棋子,可女人更像是他案头的花器,青瓷瓯或是描金碗,全凭他一时兴起。
一、宫墙外的花蒂调教
太医院的李老夫子后来写本草新编,在“梅”字旁批注道:“花蒂含铁,可解百毒。”这话若是讲给夏如意听,怕是要引出一串嗤笑。她初来那月余,连晨昏定省都支支吾吾,倒学会了东宫御花园的花语。梨树根下埋着去年采的蔷薇露,她说那些紫梗泡过的陈醋,倒能治君王微醺时的宿胀。
可这宫里的猫儿都知道,真正的花蒂调教在深夜才开场。檐角铜兽吞着月色,殿内却亮着半盏桃形灯。夏如意那年十六岁,穿着新织的冰纹杭绸,膝盖被跪得发青也不肯挪半寸。她咬着指甲说:“臣女不懂龙涎香该添多少匙,只晓得种花讲究‘见干见湿’。”
敬事房的人都说,没见过这般愣头青。直到某日酉时,御书房窗外飞进一只翠尾画眉,爪上钉着块泥金帖子:“明晨五更,御花园东角花墙。”那些年夏如意就在这般较量中,慢慢学会了与铁律共处。
二、权力的枝桠总开有毒的花
御花园的苏打霜今年改换了方子。管事太监领着十几个宫娥在暖阁磨料,碾子转动时发出令人牙酸的噪声。夏如意握着象牙圆勺,将硼砂粉筛进鹅毛笔尖粗细的瓷罐。她说这些玩意儿跟女子的胭脂一样,看起来平平无奇,可放错半分量,就叫人连呼出来的气都带着苦味。
那日晨起,端膳的银盘子啪嗒一声摔在玄武石上。三寸金莲的绣花鞋从殿角踮出来,鞋面上绣着游龙戏珠,龙须细得能穿过针眼。这等讲究,用宫女们的话说,就是“赏刑也赏出讲究来了”。
记得那年七月,东宫的并蒂莲开了。夏如意蹲在荷花塘边,袖子被淤泥浸出褐色的圈印。她说这类花最怕“滥爱”,浇多了水根就沤烂。这话若是旁人说出来,怕是要被家法伺候。偏生她说这话时,眼神淡得像漂浮在莲子芯上的露水。
三、废柴少女的反击艺术
说来好笑,这深宫里最凶险的招数,往往是那些披糖衣的甜腻话。有回夏如意奉旨进言,说了句“臣女昨夜梦见先帝”,倒把君王问得没了脾气。她跪着时辰太久,臀部青紫发红,却硬是没动半根手指去挪坐垫——这宫里头,最难琢磨的就是“度”的分寸。
那日御书房的茶盏里多了根桂枝,夏如意端着茶碗的手微微发抖。茶汤在紫砂壶里沸了三遍,香气已经淡成水汽。她说这种茶,得配着北疆进贡的甜瓜子才能喝。后来敬事房的人私下嘀咕,这姑娘倒琢磨出了套“精神调教术”——用钝刀子刮人,比利刃割肉还叫人受不了。
说到底,女人家在这世上,要么是人偶要么是家禽。夏如意偏不选这两样,她就当自己是个花匠。菜畦里的萝卜还青着,她已掐好了秋黄瓜的尖。连那专爱吃翠茎的绿蚱蜢,都被她用丝线系着逗鸟雀取乐。
四、蔷薇枝头的铁蒺藜
腊月底,御花园的墙根挖出三坛女儿红。酒坛外包着油纸,渗出的墨迹模糊成一汪青。夏如意蹲在冻土坑边,鼻尖冻得发紫。她说这种埋藏的妙处,倒像极了姑娘家藏着的心事——总要等岁月把土焐热了,才能闻见那股子醇香。
大年三十,殿里挂起新的芙蓉帐。那料子厚得能把人影子捂软,可夏如意偏要开着窗子说话。她说这宫里的寒气,跟花房里头的潮腻一个理,关得太死,根子就捂烂。那夜她端着朱漆盆替人擦手,盆沿积着层薄粉,雪白得能把人晃花眼。
敬事房的老嬷嬷如今逢人便夸她福大命大,倒是忘了那年七月,她顶着烫手的西瓜给某人送凉。她说这果子太熟,搁在水晶盘子里都蔫头耷脑,可若搁进冰窨子里待半日,果肉反倒酥脆香甜。
血与蜜的公主叙事
都说女子是水做的。可在东宫那方天空底下,水太清浅就洇不开颜色,太浑浊又沉淀了泥沙。夏如意就这么在淤泥里趟着,身上沾着淤青印子,指尖还攥着不知名的铁蒺藜。这宫里的蔷薇总爱往高处爬,可要说真的懂种花,还得晓得该在枝节处煨铁丝。
雪化后的第三天,太液池的冰面裂出一道缝,像极了腰刀切开的腊肉。裂缝边上趴着只通体乌黑的八哥,喙上沾着细碎的血粒。那鸟儿歪着脑壳,发出“报晓——报晓——”的怪叫,倒像在说:这东宫里头,永远都有着看不透的晨昏定省。






